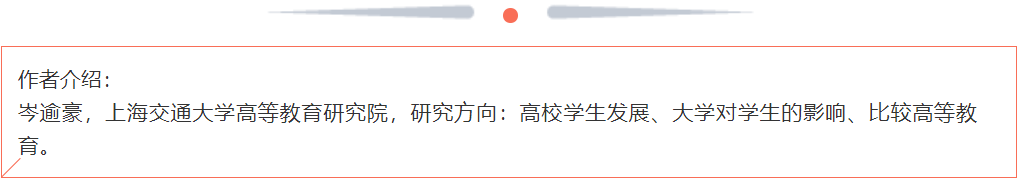學術會議是學術圈形形色色的派對。有學者將大型學術團體的年會比作心中的迪斯尼;有人視學術年會為自己的另一個家,每年此時都聚集一地探新知、會新友🏬、敘舊情🧍;有些學者更偏愛主題聚焦的小型研討會🤸🏻♂️,爭個面紅耳赤,轉身把酒言歡👩🏻🎓,換得學術情誼深。我自踏入學術圈以來,在各洲各國、高等教育各分支領域參加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不下數十次,從海報展示到論文宣講🤷🏻♂️,從圓桌討論到主旨演講,最喜歡的莫過於美國教育界幾個大型學會的年會📒。參加這些學術年會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頭腦充盈、鬥誌昂揚,但身心俱疲。我沒有參加過通宵派對,但我猜想其也有身心俱疲的效果,不過少了對視界的開拓、對腦力的激蕩、對心智的啟迪。除了正兒八經的研究展示🏇🏼、專註求實的研究者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學術會議中一段段互動小插曲——你💃🏽🦀、我、她、他——撥動著我的心弦,成為我學術和人生成長中念念不忘的回響。
撰寫博士論文那年,我參加北美比較國際教育學會(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年會,申請參加新學者工作坊👨🏼🎤👇🏻。新學者工作坊旨在幫助學位論文寫作初級階段的博士生,得到不同高校教授的指導和博士生同行的反饋。活動組織者評審申請摘要,根據研究方向將博士生和教授分組🧞♀️,每組由4-6位博士生和1-3位導師組成🧜🏽。摘要被錄用後,博士生需在會議前兩個月將論文初稿節選郵件給組內成員並提出三個問題☂️;一個月後🕵️♂️,每位博士生向其他成員提供針對性書面反饋意見🚶➡️。會議工作坊當天↖️,輪到我發言時,一位教授導師由於期刊編委會議時間沖突,不得不致歉離席。第二天開會間隙,我們在走道匆匆相遇🙅🏻♀️🧜🏿♂️,教授說 “Yuhao, I had a close reading of your work. Do you have time for a discussion?”(Yuhao,我仔細讀了你的文章📘,你有時間討論嗎🌑?)我們旋即找了一間空的會議室,討論我的研究和寫作,一抬表竟聊了一個多小時🍱。這是我與David Post教授的第一次交往👨🏽🎤🦸🏽♂️。此後多年未見,我們卻通過各種事件和朋友產生交集🍡,Post教授為我的專著撰寫的書評也將於今夏見刊。今年,Post教授任CIES主席籌辦2019年學術年會🌤,結合會議所在地舊金山的華人移民史,他特別突出征集華人感興趣的研究議題😉,並提議致敬吳貽芳——1945年於舊金山在《聯合國憲章》簽字的四位女性之一🧘🏿♂️、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學女校長🦹🏼♂️。
回國任教後🤱🏿🙌🏻,有一年我赴美參加美國高等教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for Higher Education)年會🔹,應Tricia Seifert邀請作為小組成員(panelist)準備了一個研討會提案😉。Tricia在北美高教研究界小有名氣,是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第三卷的編者之一。研討會小組的另三位成員在美國三個時區的高校任教🧑🏼🏫;我們四人經視頻會議準備討論,在會議現場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研討會結束後👶🏼,一位東亞女生走上前來,感謝我的報告為她探尋博士生涯的意義帶來了新的啟示。她自我介紹是愛荷華州立大學一年級博士生,從韓國赴美學習還不到一學期𓀅🤦🏽,是Pascarella的學生。帕是美國高等教育界的權威🦹🏻♂️,與Terenzini合編的How College Affect Students前兩卷幾乎是高教界每位學者的案頭參考書🧑🏽🎓,帕年逾70仍在科研教學崗位腳踏實地工作。Tricia也是帕的學生,我一把拉過她,脫口而出“** is Professor Pascarella’s doctoral student. How lucky she is!”(**是你的師妹🤷🏿♂️,她太幸運了👼🏽!) Tricia很自然、很真誠地對剛認的小師妹說,“Ernie (帕的名是Ernest🙆♀️,原來他的學生都親切地叫他厄尼) is lucky too, he can also learn something from you too.” (厄尼也很幸運,他也能從你身上學到東西。)此言一出,兩相對照🧔🏻♀️,高下立見☺️,我頓覺慚愧。雖然我在不同場合強調期待向我的學生學習,但這種通過西方學生發展理論和研究後天習得的想法終敵不過在東方儒家文化和中國教育環境中養成的尊卑格序的潛意識。一位是年輕亞裔女性🏋🏽♀️、國際學生、科研新手(我多年前也擁有同樣的身份),一位是古稀白人男性、講席教授、學界泰鬥,Tricia的這句話讓我重新認識了她、看到了厄尼,也審視了自己👨🦽➡️。順便說一句,Tricia的業余愛好和特長是戶外挑戰🍀,曾用不到14個小時完成了新西蘭大鐵人三項,此舉也為兩個基金會募集獎學金👰🏻♂️,促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公平。無論在科學研究👎🏿、教書育人、身體素質👫🏻、精神品質上🏑,Tricia都是我的楷模。
近幾年,由於工作和家庭原因🧑🏽🦰🧑🌾,我鮮有機會和我的研究生們一起參加學術會議,也難得有機會在學生報告結束後第一個翹起大拇指說 “Good job!”(太棒了!)🐮🤷🏿,但我相信歷經臺下無數次演練的她們在演講臺上一定很棒👎🏼🍻,把控時間、突出重點🛌🏿、衣著得體、PPT專業🧚🏻、與觀眾眼神交流、表面上鎮定冷靜。學生面向國際觀眾作英文報告尤為擔憂最後的提問環節🍰。一次和學生同去天津參加國際會議,宇晴發愁道🤾🏿♂️:“導,如果外國人提問我答不上來🏃🏻,咋辦🏄♂️?”那一刹,我想起了若幹年前自己初登學術會議講壇時我的博士生導師Heidi Ross對我說的一句話🤸🏿♂️:“You always have someone to fall back on.”(我托著呢🦶🏼!)那天🖕🏼,Heidi坐在辦公室深紅色靠背椅上,張開雙臂,做了一個往後仰的姿勢。這一刻♚,我對宇晴說:“放心,有我在👲🏻!”Heidi對我們學術會議報告的到場支持幾乎一場不落,2010年她特地南下廣西來我工作的田野支持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相較我的美國導師🦻,我對學生的精神支持顯得那麽微不足道。
如果說,學術會議上一個個頭腦裏、一場場報告裏裝的都是知識財富,學術交流讓每個人的大腦更加豐富😝、讓整個人類的知識財富遞增;學術會議上你我他她之間的故事承載的就是精神財富:支持🤹♂️、勉勵🚣🏼♂️、尊重,無論親疏、資歷、學識、地位🤒🧑🏿🍳,不分年齡、性別🔲、種族、國家,不因人而異。我的腦海中關於學術會議的念念回響👨🏼🚒,出場的👩🏿🍳、未出場的人物,親歷的、未親歷的故事,折射出一個學科、一個社會的精神財富📘。知識財富的增長離不開理性、科學👩🏫🕵🏽、探索的學術文化傳承,也離不開支持、勉勵、尊重的精神財富傳承👩👧👦。我很榮幸💍,能夠通過學術會議加入精神財富的傳承🏄🏽♂️;我也忐忑,在這支隊伍裏與眾多激勵人心者(inspirers)同行,但願自己汲取能量的同時也能釋放出我的光和熱。